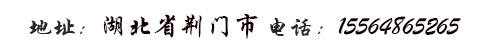一字一乾坤说仁
|
专业老牌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zd/171020/5777853.html (俄罗斯尼古拉斯·洛里奇《孔子游历》) 壹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中国人要讲个抽象的道理,总离不开山山水水的具象,就像中国诗人表达喜怒哀乐,总也离不开风花雪月一般。在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中,人安身立命需要明白的道理,自然早已彰显;人生不同境遇中的情感起伏,亦如四季中的万物盛衰,一花一草皆能与人相通相亲。 在这个精神世界中,人和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故而人能感通万物,万物也总是“扣人心弦”。这正是“仁”的根源。 一部论语,仁字出现百余次,始终处在核心位置。“孔门教人,求仁为大。只专言仁,以仁含万善,能仁则万善在其中矣。”(宋代理学家陈淳《北溪字义》)要理解仁,不如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勾画的直观场景进入。 仁者必须在艰难的登高过程中完成世界观的塑造,就像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登山者(修行者)在山脚所见为一世界,在山腰所见为另一世界,因为视野视角各有不同。然而,只有登顶后,站在最高处才能见到整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孔子喜欢讲乐,所有的道理、见识、修行都须落到一个“乐”上,才是实实在在、活泼真实的。“三月不知肉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都是体道之乐。成为仁者的过程,就是享受所见所知愈广愈真的过程。每登高一步,必自得其乐,直到看见天地万物本来一体,便自然有了“仁者安仁”的如实自在境界。 “刚毅、木讷,近仁”是登山者的刚毅;“三月不违仁”是说颜回尚未“安仁”之际的状态。仁者,不是以某种爱人的道德律令进行自我约束的结果,而是修行者在攀登的最高处看见(领会)世界一体之整全真相、进而以此为世界观的自然结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在孔子的感叹中,便有思想层面对整全的直观领会:逝者为时间、为现象、为历史,然而川依旧为川,在流变中持存自身。在变与常的一体中,我们才有可能把握河流的整全真相。 贰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说法,仁知对举,只是一种便于理解的方便。从根蒂上说,仁中有知,知中有仁,不能截然分开。如果说乐山之仁者攀登高处,善于静观世界,洞悉大全,那么乐水之知(智)者则能甘处下流,盈科而后进,周流而不滞。 然而,真正的知者一定是从山顶下来的仁者,私欲尽去,才能与万物“素面相见”,触处皆真,大知一定是仁知(性智、德慧)。相比之下,以自我为中心、以功利为导向、以算计为手段,则是“不仁”之巧知。 一部《道德经》充满对“上善若水”的推崇,上者能读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的大胸怀和大智慧;而下者却能读出工于心计的权谋(比如,以其无私而成其私)。因为,上者能以仁摄知,仁知不二。 仁知和巧知的区别在于:仁者洞悉整全大体之后,才能明白万物本就是相互依存的一体,但也各有其性、各安其位(自然差异),人在知行层面上必须守护这个一体有别的自然秩序,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巧知者则由于缺乏对整全的洞察和觉悟,只能从一己利益出发,让万物沦为向我而在的赤裸裸的对象。 《大学》倡“格物”,聚讼千载。从甲骨文字源上看,“各”与“出”正好相反,一个脚掌朝向居处(回家),一个脚掌朝向居所外面(离家)。格物,从源头上就有让物回到其自身的含义,而不是在认知中把物降格为被主体筹划的对象。 格物自始就包括了一段修养功夫,即克制认知者自身的强势地位和自我中心,以便能如其自身那般把握物本身(包括对待别人)。这个意思也包含在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中。子在川上所见之河流,就是如其自身的河流,而不是作为作为游客对象的景观河流,不是大坝建造者眼中作为能源的河流…… 西方哲学直到20世纪大哲海德格尔,才在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中有了“泰然任之”,把“被遗忘的存在”还给存在者的反思和自觉。 叁 仁所蕴含的“一体”“差异”“生生”维度,是古老农耕文明的核心生命体验,铸就了华夏文明世界观的基础,也是这个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 孔子正好处在华夏年文明的中间点,当他把仁的旗帜高高举起时,这个文明也便有了深刻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觉,照亮了此前年的文明积淀,也照亮了后来者前进的道路。所以,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者。 (唐代阎立本《孔子弟子像图卷》) 从思想根源上看,仁能追溯到更古老的易经智慧,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既是阴阳变化(作为二的差异),也是阴阳所构成的整体(作为一的太极)。“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北宋周敦颐《太极图》) 仁是易经天道智慧(整全智慧)在人道的反映,核心是把世界思为一个造化流转、生生不息的整体,而人本身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元(乾元坤元,同属一元)和仁的关系密切。明代《正字通》指出:“在天为元,在人为仁。元者善之长,仁者德之首。其文异,其理同。” 在汉字中,元、原、源、缘,都有起始之“一”(整全大体)的含义。万物本来为一体,仁者只是体“一”,行“一”。以一己为一,以一家为一,以一族为一,以一国为一,以天下为一,以天地万物为一,是登山者在不同的高度看到的不同风景,也是修道者对仁的不同层次的觉悟。觉悟越高,“一”的涟漪推展得越远。 这是一个个体觉悟的智慧涟漪,也是一个文明不断扩展的教化涟漪(或者文明的漩涡)。当这个涟漪推及最远处,固有的自我或国家的界限都自然消失,与天地万物合一,这也是“天下体系”(赵汀阳)的根源。 推展着变化着的一,是生生不息的一,非僵死不变,因为其内部有阴阳的差异,差异的转化促成着有机体的生长扩大。所以,仁便有生的内涵。宋代理学家程颢说,心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朱熹说,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 《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明儒王阳明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清儒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有变化之生,就有历史。仁者能从天地万物一体的角度看待自己,也能从生生不息的大群历史来看待自己,所以能超越一己的有限,从纵(大群历史)横(自然秩序)两个维度不断扩展自身。 华夏文明数千年“耕读传家”的传统,就是从自然(耕)和历史(读)两方面不断张大自身,并始终以家为基点,构成仁的整体。就像钱穆先生所说,华夏文明的“扩大”(大一)和“绵延”(生生)两大特点,即是华夏文明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的明证。 肆 程颢《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又云: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 程颢从浑然的“一”的高度理解仁,得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真义。从“一”的高度,才能理解,仁是其他修养(义礼知信、内圣外王)的可能性条件。 有仁,才有良知良政。《大学》提出“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内圣”之始“格物”,还是“外王”之终“平天下”,都是一个仁字。 如前所述,所谓“格物”,从一开始就有守护物之本原的含义,人和物既在一体之中又各畅其性,才是格物之正,然后才有知之正、心之正、身之正,才有国家天下之正。 内圣外王,始终是“一”以贯之。孔子晚年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芥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事浃,王道备,垂法后世焉;后儒发挥“大一统”,阐明王者平天下(王道良政)之基础。所谓“一”,就是心之本通、性之本近,“大同社会”才可能。 孟子喜欢讲“推仁心、行仁政”,就是提醒为政者推展本心之仁,与万民同心(同乐同患,同义同利),然后天下可以大治。孟子讲仁,就是牢牢抓住这个“一”,君民不二,义利不二,天下无外,所以“仁者无敌”(因为“一”够大,仁者胸襟够大,所以眼里没有外部、心里没有敌人)。 孟子重“一”,董仲舒则重“二”。《春秋繁露》开篇就点明: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在董仲舒发挥的“大一统”思想中,强调以天道(自然)秩序规范(或修正)大群政治伦理,又以大群之历史智慧(“王者必改制”)行权返经,如此构成一个天道旧法兼顾的王道秩序。只有在自然和历史(礼乐)互动中,也能有活的“大一统”之“一”,才有一体之仁。 王者处在王道秩序的核心位置,必有至大的仁者胸怀和德性。王者,通天地人三才(《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即是把天地人感为一体,函三为一,以天下观天下,才能让天下人向往、归往。王者,往也。 《周易》有同人卦,描述的就是君子(王者)如何推展本心之仁、逐渐得到认同的过程。卦辞云: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该卦从初九爻到上九爻,从同人于门、于宗、于郊,层层外推,中间也有歧路(武力征服)或不被理解,故“先号咷而后笑”。同人之道在仁在“一”,在君子之文明中正,所以能层层外推,从家到社区到城邦到郊野(未开化之地)直到平天下。 伍 《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从二。”两人能相亲,即是仁,因为性上相通;唯有彼此都能把二人感为一体,才能有亲。同时,二人始终是二人,又有别,因为习(具体文化历史社会的处境)上有差异,但也是仁的条件。没有差异,就没有仁的生机,只有僵死的同一。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的为政理想中,除了王者之“德”教化天下之外,还必有“礼教”。 礼是对自然差异的确认,并随差异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一”(性),礼也会变得琐碎繁复,失去生机。比如,五四运动批判的“封建礼教”确实是僵死的,但激活的方案应该是“复性”,而不是山寨西方现代“礼教”。 现代人往往会低估礼的作用,视之为徒有形式。其实,礼的作用主要不在行为约束之表面,发生在前观念的层次上,能生成新的底层经验。礼经得起重复,也需要重复,它和新个体的每次结合都会生出新的体验、新的作用。 本质上,礼处理的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他者的不可穿透性、不可通约性,才能激发精神活力。阴阳之道,就是他者的僵持,同时各自在僵持中变化,才有元的生机,才有生命“不透明的”的活力。 礼-敬,是和他者保持必要的距离,让事物留在其自身的晦暗或独特性中;相信事物作为他者总有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那一面。礼-敬,同时也是一种安全距离,既在敬意中保持了自我向他者的敞开,也避免了他者的创伤性冲击。自我和他者的健康互动-生成,是礼的核心。 礼也是公共空间内的教化机制、文化的具象化,能拉开参与者和自己的距离,从而战胜主体化和自恋。与之相比,当下数字空间是一个主体化、去礼化的空间,特征是招认、揭露、色情的无距离感,充满了自我肯定、自恋和主观情绪,关闭了突破自身生长的可能性。 今年4月,在北京听薛仁明老师讲课。他回忆说,他年轻时参加完爷爷的葬礼,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再也“幼稚不起来了”。这是他通过礼葬,突然和(作为他者的)死亡的一次真切碰撞,从而改变了他既有的经验结构。礼是共同经验的注入或唤醒机制。一旦失去这个功能,礼就是死的,再也不能抵达人之本性层面(乐之层面)。 华夏礼乐文明的活力,就在于礼(差异、历史、文化、守成,属阴)乐(一体、自然、本性,超越,属阳)、复礼和复性、奉天和法古、自我和他者之间无穷尽的内在互动-生成,自我更新演进。在这种礼乐之活的整体中,才有仁。 陆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华夏诗学,是礼乐(格律是礼、心性是乐)之学,本质上亦是仁学、道学。《周易·系辞》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元代盛懋《坐看云起图》) “感而遂通”正是诗学核心。心(喜怒哀乐)和天(风花雪月)在性的层次上得到“感通”,即所谓“尽心知性,尽性知天”,是诗学,也是道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以,诗人与万物无隔,天地风云皆是无言之教。 孔子论诗,讲“赋比兴、风雅颂”“兴观群怨”,其中兴是关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必有兴。在诗兴中,自然和人事、天道和人道是一种对应(感应)的关系,而不是现代修辞意义上的对象化关系,不是比喻之类思维,不是把自然缩减到人的认知范围之内。 比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其中,桃和家的关系,不是比喻关系,而是“说不清”的兴。桃之自然状态,和家的真实状态,是一种本来就有的对应关系,诗人只有把人和自然感为一体,如实感知物和人本身,才能体会这种对应一体关系中的活力和生机,才能生发诗之兴。 在这一个兴中,人心和自然始终贴近着、激荡着、生发着、回响着,而不是现成的、固定的、对象化的。仁者感物,必有兴,因为仁者虚心如悬钟,触着便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回荡不已,在若有若无之间唤出生机和新意。 仁者总是已经先行居于与天地万物如实共在的整体之中。他无论走到哪里,看见朗朗乾坤、悠悠人世、风花雪月,都觉得亲切,都觉得和自己息息相关,便有了诗人的兴致、士人的志气。在华夏文明中,无论哲人、诗人、王者,都首先是至诚无私的仁者,共享着同一种光明喜悦的人格,上与星辰近,下与世间亲。 柒 仁的根基在家和孝。如果说,仁者乐山的最高境界在山顶的话,那么的修行在山脚下的起点就是家,就是亲子关系。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之重要意义就是作为体仁的起点。 家庭-亲子关系,既有自然的维度,又有人伦(历史文化)的维度,其中有最原初的“你我”(差异)“我们”(一体)的关系体验,有最原初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超越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家是每个人之存在的“先验结构”。 从恋爱(男女)到婚姻(夫妇),再到生和育(父母),这是一个人走出(原生)家庭再归属(新生)家庭、不断扩大自我的自然过程,和道德修养中“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过程同源同构。这个过程不是受制于外力或自我约束,而是因为仁及爱本身所具有的生机的自然推动,并转化为自觉,形成了道德意识。 《诗经·大雅·下武》云:“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在每个人的成长中,家庭之爱都在很深的层面塑造着我们的知觉、话语、思维方式,这种影响是一种原初的“兴”,让后天意识的对象化的各种边界得以确立。具体而言,长对幼的慈爱,更多是自然之爱;幼对长的孝爱,更多是意识自觉、道德修炼,所以才更为重要。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开篇讲完“学”就讲“孝”,就像《礼记·曲礼》开篇讲“毋不敬”,因为事亲能孝,心才能居敬,而居敬是修养之基、入德之门。 “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程颐)亲情之孝,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的种子(仁),假以时间和培育,就能生长出道德的参天大树。 华夏文明始终扎根家庭,以“亲亲”为源泉、以“礼乐”教化大群,把家国天下同心圆化,层层推展,如生命的年轮,故有不竭之生机。《礼记·礼运》在描述“大同社会”特点时就包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可见,亲情之孝,只要“不独”(推己及人),可以自然推展出对国家、天下、天地之孝。家国天下一体贯通之情思,非仁者不能有。 相比之下,华夏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中非常在意打破这个家庭血亲联系,通过亲子献祭、出家、弑父等方式,走向对自身的超越和净化,拥抱彼岸和信仰。把家庭(贬低为私之源)与信仰、公义、独立等对立,这本身是不仁的思维方式,缺乏以“大一”和“生生”之高度化差异为生机的智慧。 捌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章句上》) 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进程,我们通常概括其精神层面为“祛魅”(马克斯·韦伯),就是把个体从其原来扎根的存在中拔出来、变成现代性主体的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失去根基和生机的过程。 “祛魅”导致大量飘荡在空中的、有自由无生机的、自恋同时又抑郁(既沉溺于自己又厌倦自己)的现代性主体,在数字虚拟时代达到极致。自恋的泛滥、爱欲的缺失、他者的消亡、竞争的冷酷……现代人只能依赖过度社交、过度信息、过度消费、过度欲望、过度占有,获得一点点精神层面的刺激和存在感。 这样的主体和自然、亲人、时间等都失去了真实的一体感,失去了感应外部变化和自身变化的生机、失去了对他者刺激的健康反应,陷入“不仁”之境。中国医书将四肢萎痹不知痛痒,四肢不能感通为一体,称作“不仁”。 医治“不仁”的重点,不在输入某种意义或价值,因为任何现成的“普世价值”都会凋谢(对任何一种价值的偏执最终都会走向这种价值的反面,比如“你要自由”“你要享受”……),重要的是恢复生机,是不断能生成的活秩序(礼乐之道),无论对个体还是大群。 生命有根基,就有生机。生生不息的意义发-生机制,只能在仁的“大体”中,在天地万物、亲子人我的同在、交织、共振、变化之中,在未消逝的过去和已到来的将来的交融互摄中,人的每一步才有新的涟漪、当下的领悟和新生,生机盎然。 当孔子谈论仁或更具体的礼乐、六艺、亲亲时,他并非重在讲授某种概念化、对象化的道理、价值或知识,而是在更深的层面注入或唤醒一种生机——意义发-生机制。他教化弟子,总是“因材施教”,重当下之“几”,让人当下领悟,既明整全又见分别,才有可能进入一多互融的生机之境。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引导他人体仁达仁,因人而异,注定艰难。所以,孔子讲话之节制、谨慎、机变(讱)在《论语》中随处可见。这本身也是仁者之智。孔子述而不作,微言大义,因为他对论述和著书(对多数人不加分别地讲同一个道理,如现代启蒙)之危险了然于胸。 西方近年现代文明,一浪接一浪,在虚无中越陷越深。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从私欲私利(第一次浪潮,以霍布斯、洛克思想背景的资本主义运动)、理性公义(第二次浪潮,以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为背景的社会主义运动)到历史(第三次浪潮,以尼采为背景的纳粹运动),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找意义的根基,建立美好的社会,却不断陷入失败。 他们始终共享着一个封闭的现代性主体的假设,把其局部特征作为基础,总是低估了他者的建设性作用(后现代主义者则走向了另一个解构自身、拥抱他者、最后一地鸡毛的极端,同样是缺乏生机的)。仁者的思维,本身与现代性主体截然不同,不是去魅,而扎根,同时具有层层扩展之活力,具有敞开自身直面他者之积极作用的机理,从而在互动-生成中获得生机。 仁者安仁,从大处看,他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理念认知,也有“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政治理想;从小处看,他有“孝弟安家、诗书育德、礼乐修身”的切身体会。“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所以,仁者不忧,无往不自在。如果从仁的角度看现代性危机,或许我们能“别开生面”。 .5.15 (清代弘仁《天都峰图轴》)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goue.com/hjbhjb/7942.html
- 上一篇文章: 元人民币在新西兰都能买些什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