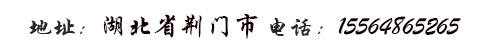散文关于南方N个岛屿的旅行记南极科
|
关于南方N个岛屿的旅行 ——记南极科考 作者:沈爱民 制作:军旗工作室 本文中所有照片来自笔者 厌倦了,会背起背囊上路。 厌倦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停车拍照的随团旅游,于是会选择自助游。如果还厌倦了欧洲教堂、亚洲寺庙,不知在世界哪个角落,可以让心抛锚时,那么,跟我走。 打开地图(比例尺大一些的),看南美大陆,在最南处有个阿根廷的城市,名字叫乌斯怀亚(Ushuaia),从那里上船,然后去南极、亚南极的地方,找那几个岛。当走过世界最南的城市,走过地球最南的陆地,走过靠近南极的几个岛屿,走在探戈、海风和大西洋的落日之中,从里到外,人会变得干净和新鲜,像刚出炉的面包,重新放出芬芳的味道。 从上路开始。如果是个真正的旅行者,会理解我自创的这句不出名的名言:旅行,80%的乐趣在路上;剩下的20%,也不全在目的地。 从国内去阿根廷,目前没有直航的航班,需要从欧洲或美国转机。比如说可以从巴黎转机。北京到巴黎,10小时20分钟的航程,大概是多公里。挺长的。不过,还只是开始,所以,这是一个有些漫长的旅程,有些难度,有些冗长。当然,没有什么是轻易可以得到的,特别是难忘的东西,比如某些感受。 布宜诺斯艾利斯 既然途经南美,就不能不说阿根廷。南美A(Argentina阿根廷)B(Brazil巴西)C(Chile智利)嘛。要说阿根廷,就不能不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是地理上,还是心理上,旅行者都绕不过也别绕过布市。 从巴黎到布市,1.1万公里航程,要飞13个小时。在大西洋的米左右的夜空中飞行,南美的味道已经开始弥漫。 机舱里一片安静,一片漆黑,只有系紧安全带的黄红指示灯星星点点。周围的人睡得颠三倒四,我没有睡意,带着耳机,感受飞机在不知名的南美歌曲声中,飞过大西洋,从博尔博雷马高原的布朗库犄角切入南美大陆。我想,这片荒芜的高原上,此时应当有个旅人、猎户和农场主妇,或者是草丛中的田鼠或是原野上的驯鹿,此时正在仰望夜空,看到这架飞机在星星中孤独飞过。 人有时需要孤独,有时还需要忧郁。 对了,这就是我感觉到的南美味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味道,这次旅程的味道。 初到布市,也许会稍稍有些失望。虽说有“南美巴黎”的美誉,可是再牛也顶多就是巴黎了。这个有多年历史的南美第一大城市,居民几乎都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街道、建筑、剧院、咖啡馆、生活方式、风俗情趣,到处可见老欧洲的底子,而且是有些颓的底子,大理石建筑都是风蚀斑驳的样子。 游客转了两天,然后会说,呵呵,欧陆风情,真的很巴黎。你看科隆剧院,出自意大利建筑师汤博里尼和法国建筑师维克多·米诺之手,典型的意大利和法国建筑风格。你看这些地铁,也是南美洲最古老的了。你看,像欧洲一样,满街的人早晚都在遛狗,狗都挺大,甚至比欧洲的狗还漂亮。你看古色古香的多莱戈广场,你看鳞次栉比的咖啡馆,有人说布市的咖啡馆比法国全国都多。不过,如果冲着这些来布市,还不如直接去欧洲,去巴黎。 阿根廷有自己的特色。谁能忘了足球,那可是马拉多纳的足球,在布市打开电视,仍然随时能看到这个已经臃肿的足球之神在喋喋不休。还有牛肉,市西南角的利涅尔斯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活牛市场,而全城的大街小巷,都有烤肉的暗香浮动。不过,除此之外,好像还该有些什么。 我吃晚饭时,突然困得在餐桌上睡着了,当然只是一小会儿。然后吃血融融的牛肉,喝冰水。回住处的路上,月色昏黄,起了一阵旋风,满街垃圾随风舞起探戈。 探戈探戈。心中睡着的感觉醒了过来。 如果说,有些东西不能言说,就是探戈。有人用恶之花、罂粟之类形容,其实只说了浮在水面的东西。南极冰山的七分之六在海平面下。还有个形容,不雅,但最接近,“充满汗水与烟味,带着百合和小便的味道。”探戈是沙龙的,更是贫民的、街头的。探戈华丽而卑贱,欢快并且忧伤。男的舞者,一定要有阿空加瓜山的冷峻线条,在面无表情的放荡中释放忧伤;女的舞者,一定要像大西洋性感的圆弧波涛,极媚,媚到骨子里,可心中都是绝望。其他舞蹈是艺术,探戈不仅仅是艺术;其他舞蹈可以欣赏,探戈不是用来欣赏的,它是阿根廷人的灵魂。 有探戈的国家,是诗歌的国家,也是深厚的国度。博尔赫斯在《迷宫》里说“永远找不到门”,探戈分明就是找不到、走不出忧郁之门的阿根廷人。谁见过,一个国家的名字,与哭泣紧紧地连在一起。嚣张的麦当娜在演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时,一反常态,变得低调和节制。谁都记得,年世界杯时,这首歌的名字成为各大报纸标题,而电视上和镜头里,全是阿根廷人的长发和泪水。足球不是娱乐的么? 在这个晚上,我走过一些街巷,它们都很安静,可我也分明听得见那首曲子,在闷热芬芳的空气中吟唱。孤独有时是一种感动,忧郁也有可能是一种力量。 因此,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不去七九大道(据说是世界最宽的街道,米宽),可以不去拉普拉斯河(世界最宽的河流入海口,河流最宽处公里),可以不去里瓦达维亚大街(据说是世界最长的街道,37公里长),可以不去五月广场、玫瑰宫、方尖塔形纪念碑,但一定要看一次探戈。而且千万要看一次好的,倒不在乎是街头还是剧场,要看懂得探戈人跳的探戈。 从这个晚上起,探戈旋律跟了一路。 乌斯怀亚 国内有一个流行很广的段子:对上海人来说,全国人都是从乡下来的;对北京人来说,全国人都是下面来的;对海南人来说,全国人都是北方来的。拓展这个段子的空间,可以这么说:对乌斯怀亚人来说,全世界的人都是北方来的。 乌斯怀亚(Ushuaia)西经68°20′、南纬54°47′,被称为世界最南端的城市,还有一个别称是“世界尽头”。是不是尽头不好说,反正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在地球上兜了2万多公里的风之后,到了这儿旅程的陆地部分算是到了头。 看过一些游记,许多人把乌斯怀亚称为“令人断肠的城市”。我想,这主要是乌市作为世界最南端的城市,所带来的那种人生沧桑的感觉。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一些大陆板块的凸凹之处,特别能使人的心境陡然变化,从深处如烟生起阵阵苍凉。所以,有人觉得,这里使人特别慵懒。 据说,常可看见一些面朝海峡的窗户,窗帘后,有位女孩,或者是位老人,坐在那里写信,而且可以写上几天。也许,必须面对这样的天和海,面对这样无垠的寂寞时,才会发觉自己有很多话要对谁说。 说乌斯怀亚许多人不知道,但说起火地岛知道的人就多些,实际上,乌斯怀亚便是火地岛的首府。它见过麦哲伦船队的风帆,留下过达尔文的足迹,火地岛和毕克海峡(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分界线)名称,就是这些先哲们的命名。 从布市到这里,也需要乘3个多小时的飞机。机窗看下去,南美大地,森严浩淼,有神灵走过的气象。 这里有世界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最大的高原——巴西高原,最大的冲积平原—亚马逊平原,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落差最大的瀑布—安赫尔瀑布,最高的活火山——阿空加瓜。 实际上,在网上看过,乌斯怀亚就是世界十大灵异之地之一,可下来问了几个当地人,谁都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呵呵,身在神中不知神啊。 下飞机第一眼,我已经喜欢上乌斯怀亚,一见钟情。我到过只有几间洋铁皮屋的机场。乌市的机场也一样简陋,但绝不丑陋,用木头和玻璃搭建,接近自然又呼吸到现代元素。 小城依山傍水,前有海峡,后有雪峰,建筑迥异,街道顺着山势,波浪起伏。 每年11月到3月,是这里的夏季,人气最旺,圣马丁大街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街边精致小店很多,买了什么东西,掌柜的都向你竖起大拇指,不知道是夸你有眼力,还是说自己的货多么好。 东西挺贵的,不过,这也似乎是世界海角天涯们的共同特征。要去极地,要去攀岩,要去斩浪,所需装备乌斯怀亚一应俱全,而且名牌荟萃,这是个倚着旅游长起来的城市。 离城不远,有国家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有个标志,看着有些亲切。原来,这里是著名的长达1.7万公里的泛美公路终点。12年前,我去过这条路起点的阿拉斯加,为了去认识地球另一端-----北极。12年后,为了看看南极,来到这条公路终点。十年多少尘与土,三万里路云和月。抛洒一路回忆,不再捡起。在路的那一头时,正是仰天长啸的年纪。走到这里,想说的,想去想的,都少了很多。 天时晴时雨。据说这里天气预报员最好当,每天说“晴间多云偶有阵雨”,一般不会错。在亚马纳语中,乌斯怀亚有“观赏落日的美丽海湾”之意。 乌斯怀亚的落日,会使人想到一个画面,凄美的画面。出城不很远,就是那座世界最南端的灯塔。对国内小资一族,这座灯塔具有象征意义。多少人都记得王家卫的小资经典《春光乍泄》中的这座灯塔。冷蓝暗红,像是油画,塔影朦胧,没有指示方向,反倒诉说迷失。 电影中,曾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台北流浪青年张震,终于来到灯塔下时,说的是“到了尽头,我想回家。” 这座灯塔频繁地出现在旅游宣传手册上,城内每天有固定巴士往返。据说,只要对着它喊出心中所有不快,就会把这些不快乐彻底抛在世界尽头。我没有去。我知道快乐也好,不快乐也好,留在心里就好。回头望时,全是美丽。 我在终南之城向国内发回了明信片,上面写着“向北眺望”。 与小城有联系的电影还有很多。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导的《旅行》中,马丁·卢卡的父亲就是从乌斯怀亚踏上穿越拉美的旅程,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引起了他对整个拉丁美洲的疑虑。在大导演安哲罗普罗斯的《尤里西斯生命的凝视》中,有句话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上帝创造的第一件事就是旅行,之后是疑虑和乡愁。” 乌斯怀亚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它的地理坐标:这里是通往南极的门户。城里那个招牌上写着:智利到南极公里;新西兰到南极公里;澳洲到南极公里;这里到南极公里。因此,这里一直是南极科考和旅游的重要出发港口和补给基地,包括我国雪龙号在内的各国南极考察船队都曾在此停泊。 有本介绍乌斯怀亚的书,书名叫《世界的尽头,冒险的开始》,倒是一语道破乌市的旅游定位。 我们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找南方的那些岛。 象岛 乘安德莉娅Andrea号离开港口,船是美国人的,船名是船长孙女的名字,小女孩的相片就挂在餐厅的入口处,排水量吨,近90米长,可以搭载多人,就远洋而言,属于小船。 晚9时整,安德莉娅离开乌斯怀亚。 夜色垂垂,岸上灯火渐行渐远,直到细成天边一条桔色的暖线。今天是正月十五吧,南半球的月亮竟然也如此圆润,依在山肩,欲语还休。 正前方,一颗流星醒目的划过。 甲板上空无一人。我靠在船头,看夜空下南半球的天海交界处。 我知道前方有个岛,我心仪已久。虽然现在看不见它,三四十个小时后,我将站在它的面前,脱帽致敬。 南极洲,是最孤独的大陆,也是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从离开乌斯怀亚进入德雷克海峡(DrakePassage)开始,就走进了一个英雄史诗般的海域。此次航程,我要致敬的那个岛叫象岛(ElephantIsland),我想看望的那个人名叫沙克尔顿(Shackleton)。 航海人知道,西风带从不平息。过毕克水道后,进入德雷克海峡,不给喘息适应的机会,安德莉娅这个小女孩就一头扑进了西风带的狰狞怀抱,在蹂躏中前行。 船起伏,摇摆,转磨般向前。舱内所有橱柜抽屉都有固定锁扣,桌椅都固定在地面,但仍听见不时有东西掉下,桌上东西最后的归宿都在地上,在地上到处溜达。 美国佬的餐厅摆贵族架子,餐具均用瓷器,结果一个风浪过来,全桌的盘碗全部摔碎,餐厅的菲律宾侍者不动声色的全部换新。 两天后,从舷窗望出去,远处洋面不再有浪的白冠,这是好兆头,说明风浪小了。 天空阴霾,改乘一种叫zodiac的小橡皮艇去象岛。国内地图上,象岛也被称为海象岛,探险史上有时则被称作象海豹岛。它的位置,就在南极洲那个朝北伸出的羽毛尖的最顶端。 远远看到了象岛。陡峭铁岩夹着千年雪,洋面满布浮冰。天气恶劣,雨助浪势,zodiac在波谷涛峰中无法靠岸,只能远远望一眼了。洋面上几只海豹破浪前进。巨大黑色岩壁上站满企鹅,在风雨中一动不动。 透过雨幕,在岩石、冰雪、企鹅簇拥处,俨然看到一座大理石座的青铜雕像,在荒蛮之中格外触目。 我知道雕像是帕托船长(PilotoPardo),记述的就是沙克尔顿的故事。由于这次探险,沙克尔顿被称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领队”,这次“成功的失败行动”,日后竟成为管理学教材的经典案例,政要、企业家、机长和船长们都被要求读这本书。 沙克尔顿是爱尔兰人,年2月15日出生,水瓶座,据说这个星座的人有强烈的好奇心,喜爱自由自在漫游,随心所欲地思考,让心灵不受羁绊,在逆境中寻求挑战。还真有些说中了。沙克尔顿爵士在南极探险史上功勋卓著,南极许多海岸、海湾、冰瀑、冰架和岛屿以他的名字命名。人类的探索之旅延伸到太空后,月球南极的一座环形山也以沙克尔顿命名。 年11月,沙克尔顿的Endurance号被浮冰挤压沉没,全体28人飘流到了象岛。这里荒凉偏僻,指望有船经过,希望渺茫,无异于坐以待毙。 沙克尔顿毅然带5个人乘小木船顺洋流北漂求救。漂了公里后到达南乔治亚岛,几经辗转,在智利找到帕托船长,带Yelcho号赶回象岛。此时留在那里的22个人,靠企鹅、海豹活命已经整整天,从出发至此已经多天。 临近象岛时,沙克尔顿站在船头,大声数着岛上的人数,当他数够22时,热泪盈眶。 喜欢这样的故事,喜欢这样的人。我还记得沙克尔顿招募这次探险队员的广告:“须完成危险的任务,工资微薄,气候严寒,长达数月的完全黑暗,危险无处不在,能否安全返航颇具疑问。”这样的招募会有人应征吗?实际情况是,0多位男人竞相应征,仅27人入选。不用问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答案。 在这里,我听到了当年三桅风帆的吱呀声,透过时空看见了那28双坚毅深邃、百折不挠的眼睛,听到沙克尔顿安静地说:惟一真正的失败,是我们不再去探索。 可惜,橡皮舟在风浪中颠簸,拍的照片稍稍发虚,有些风雨朦胧,也好,这种感觉,倒是与这里的氛围契合。 奇幻岛/天堂湾 顺着南极洲的那根翘起的羽毛东侧,从象岛继续往南走两三个纬度,也就是我国南极长城站(南纬62°12′、西经58°57′)的东南方,有个马蹄形的小岛,这就是来南极最常去的奇幻岛(Deceptionisland)了。有些象北京的故宫,上海的外滩,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方尖碑,埃及的金字塔,没见过这些标志,就象没来过这些地方一样。尽管实际来过南极的本来就不多。 习惯称这个岛叫奇幻岛。奇幻其实是个平庸的名字,有多少东西叫这个名字啊,台湾兰屿,泰国普吉,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都有叫奇幻岛的岛屿,叫这个名字的还有科幻小说、电影名字、电脑游戏甚至数学游戏。 南极的这个奇幻,有时也译成欺骗岛,其实这更符合这个岛英文名的本来含义,它确实有些欺骗性——像个死火山,其实是活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喷发时,智利、阿根廷、英国的3个科考站化为灰烬,挪威的鲸鱼加工厂被吞没。 现在来到岛上,放眼望去,满地的黑色火山灰。极地朔风在捕鲸站的废墟中游来荡去。 往上走几步,默默肃立着两座坟墓。死亡是孤独的,死在这里的人分外寂寞。无人扫墓,无人凭吊,只有风从十字架上掠过。只有我们这些后来者,沉默致意。 废墟中,一只小企鹅在伸懒腰。多天真的孩子,它不知道废墟不是家园。 这个冷淡的、黑色的火山,当年激烈喷发时,把整个岛变成地狱。 现在,恐怖早已不在,若有若无地留着一些萧瑟,让欢乐的旅行者暂时收敛,让沉默的旅行者更加沉默,也让孤独的旅行者,知道自己的孤独多么渺小。 这里其实也制造欢乐。在钟摆湾海滩上用铁锨挖几下,就能挖出温泉,上温下热中冷,地面温度可达5O°C。于是,可以在南极洗个温泉浴,作为日后显摆的谈资。而且,通常船长会发给一份正式证明书,为你的虚荣提供确凿证据。 从奇幻岛继续向东南走,接近南极圈(南纬66°33′)时,就从火山地狱来到天堂湾(ParadiseBay)。这是一个绝对使人全身心放松的地方。 海湾风平浪静,船感觉不到的轻摇,像母亲的呼吸。海湾四周,冰雪扇形环绕,冰河流入,企鹅发呆,海豹在蓝冰中游弋。 我的一位同行者,不知哪个国家的中年男人,扎马尾辫,有着忧郁眼神和羞涩微笑,背着两架尼康,却全然忘记了拍摄,显然,他已融化进眼前仙境。 下午晴天,进入南极以来,第一次见到太阳。一位同伴曾多次来南极,说上次呆了五个月,才见到一次晴天。船长将船驶入一个无名港湾,风平浪静。说是让大家到甲板上晒晒太阳,喝喝咖啡。 南极阳光强烈,空气冰凉。阳光使人怠倦,冰凉刺激人清醒。 左舷前方是个白色金字塔样子的雪峰,太阳就停在它的上方,有白云轻掩,静籁无声。 水道处,有风微吹。 下午上了附近的CuvervilleIsland。这个岛岸边都是很大的光洁的鹅卵石,象最大的西瓜。我在岸边找了块儿洁净的石头,坐了下来,看远处。 远处天空青蓝,海水幽蓝,浮冰微蓝。 不时有几只洗得干干净净的企鹅从海里钻出来,抖干水,也不走,傻傻地看着我,我同样看着它们。它们摇摇头,然后走开。 同船的各国人,一路轻声细语,此时更是都在静静地看,不出声。 南乔治亚岛 找一张世界地图,往右下角看,蓝色的大西洋中,有个船形的岛,孤零零地飘着,离最近的南美大陆,也隔着差不多二十七八个经度,约公里。 这个岛就是南乔治亚岛(SouthGeorgia)。如果说,还有一些中国人去过奇幻岛之类的南极岛屿,但听过说南乔治亚岛的就不太多了,去过的中国人就更少。 当年沙克尔顿带几个人搬救兵,就是从象岛去的南乔治亚。我们沿着他的航线,掉头向北,去这个被称作亚南极最神奇美丽的岛屿。 对沙克尔顿来说,南乔治亚是拯救了他的弟兄们的诺亚方舟。 还有一层含义,南乔治亚也是动物们在大西洋中的诺亚方舟,这里动物之多,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从象岛去南乔治亚,大约需要近两天的航程,而且要重返西风带。次日下午,在甲板上走了走,已经可以看到海鸟了,像是海鸥或蓝眼鹈。如果是它们,则说明离陆地或岛屿不远了。据说海上遇难后漂流的人,看到这些鸟,就知道命又捡了回来。 几只信天翁绕着船飞,它们是导航鸟,可以在汪洋中把船引向陆地或岛屿。这也许是传说,但它们深得航海人的喜爱,号称世界飞鸟之王,两翼伸展,可达3米,日行千里,且飞得优雅。看它飞的时候,你也想飞。 傍晚时分,远远看得见南乔治亚了,黑白相间,偶见绿色。岛身上的云很有些奇妙,漫卷西风,似乎是不经意地甩了甩,把一袖云彩抖到了海里。 我们在CooperBay登陆。登陆前,船长还给每个人发了张证书。这个岛有点来头,当年大探险时期,是捕鲸基地。直到现在,还是英国和阿根廷的争议之地,目前归属英国。 这个地方果然有点邪。海上是冰山漂浮,陆上是芳草萋萋,到处沼泽湿地,蚊蝇丛生。从岛上看海上,极地风光;从海上看岛,亚热带感觉;上岛一走,弥漫着热带雨林的气息。 不夸张的说,几乎每蔸草棵后,都躲着几只窥视你的海豹,到处是它们发出的恐吓、呼朋唤友也许还有求偶的怪声。这情景像是在一个梦里,而且是有些怪异的梦。 我在山上摔了一跤,一身泥,到海边去洗,不时从海水里钻出几只海豹,把我挤开。 第二天上午,在岛北边的安德鲁湾登陆。厚厚一层草毯,踩上去柔软,走起来一弹一弹的。走了很久,最后来到一个湖。随船首席科学家Kim曾介绍说那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湖。 其实,湖不大,也不好看,甚至平庸。湖边,Kim见到我,一脸陶醉地问,湖是不是很美?我不好打击她的情绪,笑笑,点点头。其实,这也不完全是违心,这个湖好在完全自然,就是生下来时的模样,没被化过妆。 中午时分,来到BarffPeninsula。开始对这个地方没注意,抵达时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巨大的象海豹(ElephantSeal)盘踞在那里,像一堆肉山(象海豹体重可达6吨),对来客眼皮都不抬。更吃惊的是,满山满谷的王企鹅,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照片上也没见过,据说这一片有30万只。 王企鹅雍容华贵,身披银色礼服,胸前金红领巾。好看是好看,可太多了,像古代排出阵仗的士兵,也像土著人的包围,涌过来把人踩成泥像是很轻松的事情。它们还特别爱往人身前凑。 王企鹅的叫声似乎很有规律:6.I1.35-I,这是我写的企鹅叫声简谱,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这些东西,似乎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只是站着、睡觉、交配和唱歌。 人们有个误解,认为企鹅苯苯的。曾经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当飞机飞过头顶时,企鹅抬头观看,但不会转身,只会向后仰着看,当飞机飞过时,它们会纷纷向后摔个仰面朝天。事情弄到最后,英国皇家海军郑重其事地派出研究小组,进行了17次飞行试验,结果没看到一只企鹅因看飞机而倒下,证明这个传说纯属子虚乌有。 四周环顾,前面是漫山遍野、“鹅山鹅海”的王企鹅,后面是巨大狰狞的象海豹,旁边不时有小海狮冲你低吼,头顶上低旋着褐色贼鸥,远方冰川下是群群驯鹿。真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回去后,如果有人问我,看见企鹅吗,我就轻描淡写地说,见过几只,然后把BarffPeninsula的照片打开——一定把人吓一跳。 临近黄昏,来到格里特维肯(Grytyiken)港,这是岛上少数居住地之一,号称南乔治亚的首府——其实就是几间小房子——当年的捕鲸基地,也是沙克尔顿当年找到人的地方,现在这里还有他的墓和破船。 路边的沟里躺着庞大的象海豹,南大洋生物特点之一是生长慢,代谢低,个体大,寿命长,但它们躺在沟里显得过于大了些。就那样不体面、不协调地在沟里,像村边土路旁的狗。 这里竟然还有座小教堂,在暮色中亲切地候着我们。一行人渐近,不意间响起了悠悠晚钟声。于是,荒野有些温暖了,有了灯火的意思。 第三天上午,去FortunaBay,天气突然大变,风大浪急雨狂,小艇依然出海。我乘第一艘艇出去,海浪抽在背后,像石子打来一样。上身穿omni-shield面料的冲锋衣,防水还透气,据说是与老牌的Gore-tex面料差不多。 登陆没多久,雨停日出,荒野间淡淡现出一抹彩虹。远方山脚下,有鹿群经过。 回来的路上,我走上一面草坡。走至山坳处,一阵风吹来,且有动静,急回头,风起处,一队驯鹿四蹄腾空从身边掠过,瞬间远去,像一缕轻烟。我目送它们,蹄声鹿影,令心情陶醉。 下得山来,眼前是蓝色大海,万籁无声。那盘旋的信天翁呢,那飞扬的枯草屑呢,来时的欢腾都已不见,原野恢复寂静,一如什么都没来过。 身后,不觉间,有只褐色鸥鸟如云轻落。 马尔维纳斯 由于风暴不邀而至,临时决定提前离开南乔治亚,驶向马尔维纳斯群岛(Is.Malvinas)。 这段航程,在南纬52度左右横切20个经度,约公里。我估计不足,以为是一天半到两天的航程,结果整整走了三天三夜,而且大部是在风暴之中,成为出发以来最难熬的一段航程。 昼夜中,无论何时看舷窗外,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景——灰蒙蒙的天空与无边大海,没有陆地,没有岛屿,没有船帆,没有飞鸟,也没有阳光,像个一辈子只画一张画的画家作品。 浪高7到8米,我躺在四层船舱的床上,仍看得见浪头拍在舷窗上,撞击声如木锥攻城。对面床上的人,随着波浪压下,弹起。 开柜子、上卫生间,都成了有些危险的事情——说不定被甩到哪里去。地上已经狼藉一片。但每当有大浪袭来,总还会有东西掉下。下一次该是我吧。 上了一次卫生间,懵懂中,像是听见吹口哨声。 谁在风暴中吹口哨呢。 第三天,天开始放晴,风浪小了,马岛也终于快到了。由于风暴原因,船延迟10个小时到达。 当安德莉娅缓缓驶入马岛首府斯坦利港(PortStanley)时,已是暮色四合之时,在引水船的引导下,远远看见岸边的万家灯火了。 岸边的草地上,不再是企鹅和海豹,而是牛群在吃草。这是上船以来,第一次看见正式的居民点,说明我们离南美大陆不远了。 在斯坦利港进行了所谓干登陆,不用穿靴子下水,直接上岸。此时已是晚上八点多。 说起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恐怕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英阿年的马岛之战,这场战争是现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英国战胜,该岛目前由英国管辖。因此,上岛之前,我对这个群岛的全部印象还停留在马岛战争时,结果一上岸,才发现恰恰完全相反。 斯坦利港这个小镇,太安静了,那么多房子和街道,仿佛都不说话,只有纱窗后面的灯光,告诉你这里也有许多故事在发生。 确实有过许多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告诉我这种祥和可能只是一个表象。詹姆斯·派克,第六代英国移民,岛上惟一的职业画家,其父特里·派克是英阿之战时的英国战斗英雄。詹姆斯与阿根廷女孩玛丽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不幸相识进而相爱(我竟然使用不幸这个词),玛丽亚移居马岛并怀孕,医院却拒绝为玛丽亚接生,教堂也不同意他们在教堂内结婚。后来的结果,是两人被宣布为不受该岛欢迎的人而不得不离开。詹姆斯后来对媒体说,“人们不相信我会遭遇这样的事,还以为我在编故事。” 我在这个晚上,站在那个拒绝做结婚公证的教堂前,也希望这个真实的故事从未发生。因为这座教堂显得那么圣洁宽容,小街显得那么美好干净,每家窗户流出的橙色灯影那么柔和,空气清凉,夜色透明。 马岛的安谧印象,在第二天下午进一步增强。去了CarcassIsland岛,其实这个岛没有什么,没有居民点,只有许多鸥鸟。 在雨中徒步跋涉了两个多小时。这些天基本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等我转过一个满是金黄茅草的山坡时,突然看到一个几根铁丝的晾衣场,心中倏然一暖,几行字自己溢了出来: 走过荒岛 看见了芳草萋萋 也看见许多鸟儿栖息 有的凶猛 有的美丽 在那面草坡上 晾着几件寻常衣服和 床单 海风使它们飘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 眼睛和心里都有些湿润 我对这个晾衣场按下快门,因为它的朴素。日本摄影家荒木通常被看成是低俗甚至是色情的摄影家,他的作品放荡不羁,而且有些花哨。这个号称从不流露悲痛的人,拍他病逝的妻子,却没有一丝张扬,没有一丝玩世不恭,拍得非常朴素,成为他最有力度的作品。 荒木还有一句话,让我把他与其他低俗的摄影师(这样的摄影师真不少啊)区别开来,他说,摄影是一个感伤之旅。享有盛名的北野武曾说自己不如荒木,这样说应该不仅是谦虚,何况北野武从来不是一个谦虚的人。 房子周围,是巨大灌木形成的有野味儿又优雅的绿篱笆,进他们的家,首先要穿过这些自然形成又精心修饰过的绿色拱道。 走进来,才知道这是一个私人农场,三个人丹麦人经营,两男一女。女主人做了十几道精美点心招待我们。据他们说,我们是第一批到这里的大陆中国人。 与他们告别时,我心里有些羡慕,有些怅然。旅程即将结束,又要回到平凡的城市生活。我只能在心里,在梦里,才能过他们的生活。与鸥鸟作伴。风力发电。自己养着奶牛。 马德林港 躺在舱内的床上,翻书。 这里有句话,“每当我们到达世界遥远的天际,常常问自己是谁”。我不在遥远的天际时,在家里的床上,而且是在少年时,就常常这样自问。 几十年后,不再问了,知道没有答案。倒是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有些哲学味道——“你就是你全部的生活体验”。回头看走过的路,像是一直在循着这句话走,在看,在想,在体验。 也许这果然就是生活的全部。 收拾行李,睡得晚,早上睁眼,已近七时。船已于凌晨5点多靠上阿根廷中部的马卓林(PuertoMadryn)港,一个地图上通常查不到的小港。这里有航班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公里。 多年前,由流亡的威尔士人建立了马卓林港,7万人,气温适度,白云蓝海,微风徐徐,是个不错的旅游小镇。很多人跑到这里看鲸鱼。 当地人中午都在睡觉,三点多起,然后要喝下午茶。他们慢悠悠地生活着,工作也是为了维持这种生活。 除了临海一面,马卓林后面是广袤无垠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这里没有机构和政府,只有一些脏兮兮的羊群。如同一位牧羊人挥舞着烤羊排时说的,“巴塔哥尼亚?嗯,就是任何能吃到这个玩意儿的地方。”由于遥远和难以接近,巴塔哥尼亚成为南美的香格里拉。 我朝深处看去,一只巨大的安第斯秃鹰扶摇而上,荒原之风托起它的双翼。 晚上在镇里逛,街上到处是拉美人面孔。我乱走,渐渐灯光稀少。一个美丽的刚学会走路小女孩一直拉我裤脚。街中一只瘦狗咬着自己的尾巴转无数的圈。汽车喇叭在路口敲着旋律和节奏。 我在一个自由市场买了几块石头,然后从海边往回走。这海有些象厦门的海,也有些象海南的,也像印尼巴厘的海。星星很亮。 涨潮了。 昏黄路灯下,可以看到沿海的围栏上,各种笔迹用西班牙文、英语和法文写着一些东西,都是凭栏的人随手写的,他们在公园的石椅上也写满了字。我想,这些文字,也许是自言自语,也许是诗,也许是他或她写给某个人的话。 我在雕像边靠海的石栏上,也用中文写了几个字:我在这里,来过了。 图:南极长城站 作者介绍 沈爱民 部队大院长大。年入伍,转业前在福州军区炮兵部队任营长。后长期在科技领域工作,退休前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理事。 经常组织和参加大型国内外科学考察,如发起组织和参与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先后参加南极科考、东非大裂谷多学科联合考察、亚马逊热带原始雨林生态考察、密西西比河流域科学考察、多瑙河流域减灾科学考察等。 除专业著作外,主要文学著作包括:《极地心路》、《偶尔上路》、《灯暗酒红》(该书获法国GourmandWorldCookbookAwards图书奖),《每一滴酒都不一样》。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摄影集《路上的印象》。 兴趣广泛,涉猎旅行、文学、摄影等诸多领域。 请点亮在看,鼓励一下我们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goue.com/hgwxtz/4897.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加坡这周为什么有小长假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