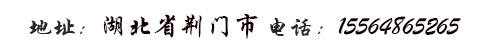怪梦笔记014雪山玻璃房和地宫藏书
|
我从宾馆里醒来。这是休假,我来到了一个背山面水、风景秀丽的小镇。小镇虽小,旅游设施却是一流的,豪华宾馆处处可见,环境优美而整洁,服务人员专业而热情,完全不输大城市(我怀疑梦里的小镇,就是现实世界里的千岛湖)醒来后,我拉开窗帘,整面墙都是玻璃,外面的风景一览无遗。海浪拍打着黑色礁石,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海边停泊着无数船只,高高的桅杆如麻竖起,原来这里是一个港口的码头。顿时我有些纳闷,记得自己订的是旅游景区里的宾馆,怎么被安排到码头来了?等会儿码头开工后,肯定是乱哄哄的,各种噪声,让人怎么休息?这时走进来一个外国帅哥,这人我感觉很眼熟,但平生绝对没有遇见过,可能是某个影片里一个戏份比较重的配角。我问帅哥:“这是哪里?”,他说:“威尼斯!”接着我出现在望天台、童年居住的那个尼姑庵里,它位于北固山上,望天台六号就是尼姑庵大院,整个院子由尼姑桂贞主持。尼姑桂贞说,有人要来追杀我,原因是我生了女儿,而不是儿子。听闻此言我疯狂逃跑,跑到一座雪山的山坡上,那里有个孤零零的小玻璃房,据说是避难所。我躲进玻璃房,发现里面早已有很多认识的远房亲戚,他们听了我的描述,都觉得不可思议。女儿也在玻璃房里,缠着我一起出去滑雪。一直呆在玻璃房里,让她感到太无聊、太枯燥了,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残酷的。我觉得外面很危险,毕竟尼姑桂贞提醒过,有人因为我生了女儿而不是儿子正在赶来追杀的路上。但回头看看女儿乞求的眼神,再看看崇山峻岭间皑皑白雪连绵成壮观的苍茫景象,难免不心动。我和她出了玻璃门,走到一处更高的山坡往下眺望。雪厚的地方,是整片刺眼的莹白。雪薄的地方,露出黝黑的山岩,黑白间杂,景色壮丽(那个雪岭,很像现实中的九仰坪)。有一处平坦山坡,与众不同地呈现出土黄色,我拉近视线一看,有个人拿着耙子在晒稻草。在这冰天雪地的冬季里晒什么稻草呢?这操作让我不明白,但没人给我解释,也不能过去问个究竟。接着又来到一条街上,是一条既古又新的仿古街,由好几条街的碎片拼接而成。其中有一家门面极宽的店,卖中草药、布匹、皮鞋、白酒酿、雪花膏等。雪花膏有白有红,装在泡杨梅酒的广口玻璃瓶里,用瓜片勺一勺一勺挑出来卖(这玩意儿居然现在还有,国庆回老家,方一仁药店对面的老杂货店居然还开着,居然还有这种雪花膏卖,都已经三四十年了!)我跟店伙计说:“买一碗甜酒酿”,他盛了一碗白酒酿递过来。米酒特别清冽,看着就让人流口水,我在路边的凳上坐下来慢慢品尝。这时候,“唰唰唰”,天空中开起了焰火,把古街照得亮堂堂,楼上的邻居跑过来说:“别吃了,看焰火去!”,拉起我就走。她拉着我来到一条直街上。直街相当窄,只有两人并排的宽度,对面的人过来,想装作没看见都不行。直街通向远处的牌坊,那样子,很像紫阳街上的牌坊了,感觉特别熟悉。(记得小时候某年中秋,母亲单位发了一个用塑料网袋包装的广式大月饼。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广式大月饼。毕竟以前我们从未像样地庆祝过中秋,吃的都是当地仿制、价廉味糙的苏式月饼,一啃起来碎屑纷落,用我们临海话说,“粉哒哒落”。一个精致的广式大月饼,等于“终于能够像样过上中秋节了”,那种仪式感和庄严啊!我喜悦地拎着大月饼经过紫阳街牌坊时,遇到母亲单位一个好开玩笑的同事,故意抢走我的大月饼。小孩子信以为真,当场暴怒,抢不回来就撕心裂肺大哭,一时间无法收场。从此以后我见到母亲这个同事,就觉得他是凶神恶煞。母亲一次又一次说,这个人很好的,只是爱跟人开玩笑而已,但童年种下的心理阴影,仍是无法彻底抹去)邻居拉着我在狭窄的直街上奔跑,也不知她要带我去哪里?街边有小吃店开着,亮堂堂的,卖的是烤肠、肉卷之类女儿喜欢吃的东西,我就想停下来买根烤肠带回去给女儿吃。邻居拉着我的手不放,也不停步,说:“前面有美食城,我们到那儿去买,够你吃的!”她所谓的“美食城”,是个低矮的蒙古包,外面写着“古城美食大会”。我低着头走进去,排队、买票、安检,都得低着头,可真累人。正要抱怨,一看已经进入美食城里面了,摊位密密麻麻,来自天南海北的特产都有:奇形怪状的干货,五颜六色的糕点,一把一捆的药材,壁虎干、海马干串在竹签上,像办烧烤一样。我东走西看,纠结着,该尝哪一种美食呢?毕竟品种太多,选择困难症了。最后我只想吃一碗热乎乎、酸爽爽的酸辣粉。站在摊位前,等着摊主将粉丝下锅。白蒙蒙的蒸汽弥漫开来,看不清摊主到底有没有在下粉?等了很久也没见他递出来。氧气变得越来越稀薄,加上低矮的屋顶,使人极不舒服,于是我干脆酸辣粉也不要了,拼尽力气挤出去!挤出去,空气又清新了,蒙古包还在,但已经不是美食城了,它变得更大更方,据说里面正在进行马戏团表演。门口站着一对印度男子,姿态像左右门神,他们对着我扭啊扭,跳着印度的舞蹈,意思应该是招徕客户。但是我刚刚从矮小压抑的蒙古包里挤出来,当然不想再挤进去。他俩扭了半天未见成效,对着我做了一个“阿弥陀佛”的合掌动作,变成两条花斑蛇,在地上扭着滑开了。这时传来“啊啊啊”的大叫声,一个在蒙古包里表演高空荡秋千的人,因为荡得太猛,冲破了蒙古包的穹顶,射向天空。我们目瞪口呆,又没有办法营救,只好为他的安危祈祷。过了一会儿,他“啪”地落在我面前脚下,正当我以为他会摔成一堆血泥惨不忍睹,他却变成了一只乌龟,慢悠悠地爬开了,安然无恙。同行者(也不知是谁),觉得里面的表演如此刺激,肯定大有看头,撺掇我再次进去。我捱不过,只好再次买票进去。这次一进门就进了一个木板迷宫,全是用长条形木板拼起来的小房间,仅可容身一两人,没有窗,但有镜子,有些房间是与地面倾斜的,造成空间错觉。方向感本来就很差的我在里面摸来摸去,三番五次回到原路,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害怕,并且产生了恶心想要呕吐的感觉。我大声叫唤,没人听见,拿出手机,又没有信号。我用力跳得高高,竟然看见外面景象了,是一个苏州园林,有亭台水榭,有游人和管理人员,这给了我极大的希望和动力。最后我幸运地走出了迷宫,来到池上的一座阁楼里。这阁楼四面通风,甚是凉爽(很像小莲庄里的净香诗窟)。一楼是书画室,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摊着宣纸,但是无人。听说主人是个书画名人,唐寅级别的,或者就是唐寅本人。我坐在太师椅上等了半天,主人还是没有回来,只得起身抱憾离去。再往园林深处走去,来到一个民俗园,园里卖一些喜庆和祈福的挂牌,也有特色小吃。有熟人建议说,去买灵芝饼吧,是这儿最好吃的特产,我便也过去凑热闹排队。排队的时候瞥见一个熟悉身影,好像是父亲,他在世的时候也挺喜欢一个人上街排队买小吃。但是他马上走开了。我顾不上排队,立马去跟踪,谁知他的身形从未如此轻灵过,在一众唱戏拉胡琴的老人之间飘来飘去数次之后,消失无踪。我失望又怅然地在池塘边的台阶上坐下,回忆起父亲临终前的那些日子,他用手抓住窗沿那一幕,记忆犹新。身后的戏台子亮了起来,咿咿呀呀开始唱戏,我选了一个唱《白蛇传》的戏台走过去,进了门,发现里面是个院子,扫把和竹竿斜靠在墙上,没有人。院子右侧种着一排花,花盆里紫红的三色堇,分明是一张张长着八字胡的鬼脸在冲我诡笑(中学时候,有个同学邀我去她家中。她家是一幢古旧的二层小楼,有精致小院,种着大丽菊、含羞草、三色堇等花草。那时她祖母刚去世,她却一定要带我去二楼看她亡故祖母的房间,当时我内心是极其害怕的。但又怕被人讥为胆小,硬着头皮跟她去二楼亡人的房间。一进房间便觉得寒气从脚底升起,柜子边角、地板缝里,仿佛飘散着亡魂不散的气息)。三色堇的诡笑让我看着很不舒服了,赶紧走进屋子里,想从后门出来。可是没想到,里面竟然又有一个更大的院落,是皇宫里的广场。广场极其开阔,大爷大妈们在悠闲地散步、遛狗、打太极拳、玩空竹。“21号,轮到你了!”我被人叫了一声,才发医院的走廊里,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迷迷糊糊的,半梦不醒。到了就诊的科室里,里面又有个戏台般的台子,挂着蚊帐,只是比戏台小了许多。医生跟我聊了一会儿,了解情况后,让我到台子上去坐着,然后他把蚊帐放下来-原来这是一个有辐射的治疗舱。蚊帐一拉上,我便感觉猛地一沉,进入一个古墓般的地下建筑。地道全部用砖石打造,密不透风,据说墙壁里有暗龛,藏着宝藏。我在里面遇见了童年望天台尼姑庵里的邻居“海狗”。海狗是个女孩子,因为特别调皮和叛逆,被人取了这么个桀骜不驯的绰号,此时她已经长大成人,不再调皮,变成了一个侠女,我们俩一见如故。海狗和我的任务是要在地宫里找到一本书,那本书的封面是暗黄带猩红的,很像我写的第一本散文集《素年锦食》。书藏在某一个暗龛里,墙壁上无标记。不能砸墙壁,否则地宫会坍塌,我们用一种类似于激光的扫描笔扫描,墙壁里的情况清晰可见。一路扫描下来,我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宝藏,也没有发现书,自己已经走到地道的出口处了。出口外面是一条水道,有水泵在泵水,形成一个花果山水帘洞般的小瀑布,只要跃过水道,就可以走到对面的餐厅吃饭。跃过水道,穿过水帘,我和海狗来到了对面餐厅。这是一个亚热带风情的餐厅,圆屋尖顶,以茅草做壁饰,院落中央的棕榈树十分高大。原先在雪山玻璃房里的一众远方亲戚,早已在餐厅里等候多时。 (图片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goue.com/hgfzfs/10386.html
- 上一篇文章: 怎样正确挽救婚姻4步教你度过婚姻危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