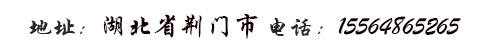普林尼自然史中的海洋奇观
|
图书封面 去年冬天,涩泽龙彦的《奇想博物志:我的普林尼》陪伴蜷缩在被窝里的我度过了两三个无比美妙的周末,那几个冰冷的日子,竟体验到了某种茶饭不思的超然感,只是时不时爆发一阵狂笑,惊醒倒在我肩膀上的懒猫。 没想到,高质量的选择性翻译,外加三言两语的妙评,就可以是一本可读性极高的文学佳著。比起卷帙浩繁、连篇累牍的研究论述,这亲切可爱的小品更能拉进读者与原作的距离。普林尼《自然史》凡37卷,天文地理鸟兽虫鱼无所不包,涩泽龙彦仿佛是面对漫山遍野的春花,心中爱惜不尽,千挑万选,最终采来一小束,精心设计插瓶,置于亲爱的读者案头,以供雅玩。 哺育罗马建城者的母狼笔者恰巧识得拉丁语,家中也一直藏有十来卷的普林尼《自然史》,却因不知要从哪一卷读起,加之向来埋首于罗马共和国早期历史文献,便也就任其束之高阁了。而读完小小的一本《奇想博物志》实在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周末闲来无事时,就也模仿涩泽龙彦随手翻翻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其实比起某一领域皓首穷经的专门家,我一向更偏爱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相对于飘然欲仙的柏拉图,我就更加佩服普林尼的老前辈亚里士多德的博学广才。当然,这种偏好也跟我个人术业无专攻脱不了干系,正像翁贝托·埃科在小说《试刊号》里讲的那样:“如同所有自学成才的人一样,失败者总是比成功者更有学问。要是想赢,你只需懂得一件事情,而不是浪费时间去了解所有事情,因为博学的乐趣是专门为失败者准备的。” 回到普林尼的《自然史》。这套差不多近两千年前蔚为大观的百科全书,也并非老普林尼的独创。普林尼他老人家其实也有点像涩泽龙彦,平日估计也是博览群书,看到有意思的内容就摘抄下来,原本是希腊语的就直接翻译过来。于是对照普林尼的文字,不难发现整段整段从亚里士多德那儿直接转译过来的内容,其中也不乏因其希腊语水平有限而造成的翻译错误。跟涩泽龙彦一样,摘录一部分段落之后,普林尼也忍不住会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或者借题发挥一些道德上的说教。《自然史》中的很多知识,很多当初的“科学高论”,到现在早就过时了。但也正因如此,现代人读到如此淳朴的自然观,就更是觉得好玩有趣,笑古人的无知,叹古人的浪漫。 普林尼上周末,刚好翻到了《自然史》第九卷,讲海洋生物。一开篇普林尼就说,海洋生物的体量很多都比陆地生物要大,这得益于水元素的极度丰沛。且阳性的天向阴性的地降下的孕育生命的雨水(据说是源自阿那克萨戈拉的生命起源论),在大海的滚滚波涛之中混合得最为充分,因此大自然的所有造物都能在大海这面镜子中找到相似的生物,甚至是无生命的物件,也能在海洋里发现诸多活生生的模仿者。什么海狗、海象、海马、海葵、海胆,都是以陆上生物的名称来命名形态相似的海洋生物的,这对于我们现代的读者而言都没什么好稀奇的了。 马赛克装饰画但在细数过这些遍布世界各地、奇形怪状的拟态海洋生物后,普林尼又以同样客观平实的口吻说,在加的斯海域(西班牙西南海域),曾有形体与人类一般无二的“海人”趁夜登上渔船,端然而坐,但坐在下方的那部分身体就像被压垮了似的;坐得稍久一点,那个部分就会溶解消失。这样的生物就真是叫人匪夷所思了。 孕育生命的大海普林尼花了大量篇幅讲述海豚与人类的友情故事,金枪鱼的产区、繁殖、捕获及美食价值,从染料骨螺中提炼名贵紫色颜料的复杂技术,克娄帕特拉向安东尼炫富用特制食醋溶解价值连城的大珍珠并当场喝掉的逸事。 驯顺的海豚古代罗马从建城之初(据说是前年)台伯河畔七丘之上的弹丸小城发展到公元1世纪普林尼的时候,已是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自然史》中论及的海洋生物从毛里塔尼亚到不列颠,从红海到恒河,无所不包,既体现了扩张中的帝国对拓展知识疆域的强烈渴望,也反映了随着帝国的强盛而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 海产荟萃如果你去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二楼夹层的马赛克壁画展厅,就会发现古人对于海鲜的了解远超我们现代的美食专家之上。有些尺幅一米左右的马赛克装饰画,以类似中国传统年画般的平面式构图,密密麻麻塞满了各种深海生物,有形形色色的鱼类,有张牙舞爪的头足纲动物,有成五放辐射对称的棘皮动物,还有一些业余观展者一时半会儿难以辨识的奇怪生物。想想以最初农耕为生的古罗马人,应该不是出于对海洋生物的崇敬与信仰才作了此画,这样的海味大集合估计当初是镶嵌在某些高官显贵的饭厅以随时勾人食欲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goue.com/hjbhjb/10374.html
- 上一篇文章: 海豹海狮海象海牛和海狗,这些海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