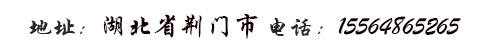水母
|
如果我们睡了,我们就是他安静的宝贝 如果我们醒了,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宝贝 如果我们哭了,我们就是他雨滴构成的云彩 如果我们笑了,我们就是他的闪电 如果我们愤怒争斗,这是他的神遣 如果我们平和宽容,这是他的爱 Chapter1 公元年前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党同伐异也日趋严重,终于导致灭世之战爆发。瞬间高温令地表熔结成一整块,整个地球沦为炼狱,只剩下灰烬、氢熔玻璃岩和辐射云,亿万生灵几乎毁于一旦。随即,浓厚的辐射尘遮蔽了太阳,导致气温骤降,六月飞霜亦属寻常。即便少数侥幸存活下来的物种,也因遭受严重的核污染而发生了变异。 眼下,拳头大小的雪花自高空坠落,最初裹着空气中的尘埃,又砸进灰堆里,融成大滩淤泥。雪越来越大,越来越急,渐渐的,将地表彻底冻住。再降下来的雪,便不见沾染任何污秽。放眼四望,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往日灰茫的荒野竟没有了一丝杂色,圣洁,娇柔,犹如一具具庞大的女性胴体,沉睡着。整个天地间,唯独某个山谷里,一溜儿简易窝棚,屋顶压满雪,门窗却还遮挡不住,在白里陷出一只黑眼球。 雪后清晨,天光微熹,天空少见地透出一小块婴儿蓝。丁零零——丁零零——,宁谧天幕下,一头骆驼打着响鼻缓缓行来。这骆驼受过辐射,通身纯白,连驼峰都白到几近透明,只皮肤褶皱处幽微发蓝,更显得那白更白。男子跨坐在它背上,穿一件纯白羊皮袍,面罩上落满了雪,若不是那一双深蜜色眼睛间或一眨,乍看之下竟像隐了形。 这远道而来男子,在岭上勒住骆驼,朝窝棚方向眺望了一会儿。地面原有大风吹成的道道波纹,这雪一下,便将波纹定住了。这样一片阒寂到近乎庄严的静海,简直令人疑心,鸿蒙之前它便是如此存在着,宇宙热寂之后仍会这般存在。 天太冷,他吁了一口气,随后绳索一抖,那骆驼鼻孔喷出大团白雾,悠悠然往岭下走去。骆驼屁股上大包小包的行李,和着步伐一颠一颠,跳脱得很。 一阵剧烈的咳喘,正将少女从深深的噩梦中拔出。回想刚才,每寸皮肤、每根毛发、每个细胞,都被巨大的黑石板压住,分毫动弹不得,呼吸亦被牢牢钳制……她拼尽全力,想将黏合的唇起开一点,然极度干涩,舌已石化,声带也全不听使唤。是徒手攀岩吗,但怎会置身在这样光滑的夹缝中?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挪移寸分,除非变作壁虎。到后,那石板竟从四面八方缓缓压来,眼看人要挤成肉酱了,急得鼻翼鼓噪,指尖抓挠,眼球越转越快,徒然发出呕呕的喑哑声,偏偏就是醒不来。此刻她抱住双臂,深深吸进一口气,再缓缓喷出。空气中有一股难以言说的呛,像是混合了汞和洋葱的狗屎味儿。原来睡到中途,空气净化仪坏了,难怪差点憋死。她慌忙捞过呼吸面具,这面具由几片锈铁皮胡乱焊成,只留了眼、嘴和鼻上几条细缝,戴上之后,任凭再漂亮的脸都像铁皮蚱蜢。不过内部有一层网,涂着一种特殊的纳米物质,可以隔离辐射、净化空气。简陋的卧榻,床单被褥早已脏到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纹理,靠近床脚一端的墙上,电屏抖了两下。有那么一瞬,她以为出了故障,还没来得及高兴,那男人口眼一斜,随即又恢复了正常。“早上好,亲爱的!现在是地球历年8月24日,按照古中国的说法,今天是处暑,也就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哦。怎么不说话,今天的你可有点怪哦——哈哈,是怪可爱的啦!哥呢,哥今天拥有了一个超能力——超喜欢你哟!”“闭嘴!”她低吼着,嗓子眼里泛起一股金属的苦味。什么哥不哥的,明明声音活像猫叫春,还一刻不休地饶舌:“你会弹吉他吗?不会啊?那你怎么拨动了我的心弦?你有打火机吗?没有啊?那你怎么点燃了我的心扉?你是什么血型?A型?B型?AB型?还是O型?不,都不是!你是我的理想型……”她四下里摸索,抡起一只扳手,卯足了劲朝电屏正中掷去,哐铛一声,不偏不倚砸中那男人的鼻梁。然而电屏毫发无损,扳手徒然弹到她的大脚趾上。她吃痛,气极,挥舞一把铁锤,扑上去就是一通猛砸,直砸到自己气喘如牛。这自然也是蜉蝣撼树,电屏上一点蛛丝马迹都没能留下。偏偏这屏嵌满整面墙,要是不想砸塌这个小小窝棚,恐怕也只能听之任之。她掀开面具上的进食孔,朝他吐了一脸唾沫,又迅速阖上了。这少女近乎全裸,骨骼匀称,线条流畅,污垢的皮肤、打结的头发、锁骨、腰肢、腿弯间,溢出重重热力,面罩后面,一双毛茸茸的黑眼睛正恨恨朝外瞪视,莽撞与纯真,颇像一头暗夜密林中,凝望火焰的小豹子。男人目睹了这一幕,幸灾乐祸的笑意几乎掩饰不住,嘴上仍是油滑不减:“亲爱的,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是宇宙大盗吧,他们联手把银河系的星星都偷来,放在了你的眼睛里……”“操你大爷的银河系!”她咒骂着,起身哗啦拽开帘子。那帘污腻不堪,几乎已烂成了布条。可外面什么时候竟落满了雪,只能朦朦胧胧辨出五六个一色一样的窝棚,一间搭住一间,胖鼓鼓的,朝雪地里延伸。难怪时候尚早,天光却较往常亮堂。平日里,都是辐射尘遮天蔽日,起风时,如果风够大,将辐射尘掀开一角,人恰巧又在这个时候极目远眺,才能影影绰绰望到一长列墓碑,黑压压地勾勒着地平线——那是曾经的摩天大楼,早已被拦腰掩埋,半点灯火也无。不知是不是眼花,这会儿在一片白茫茫的雪色后面,她居然看到,那高楼顶端似有荧光一闪,暗橙色,像谁点燃的烟屁股。一眨眼,又看不到了。驼铃越来越近,越来越明确。前院里传来孩子们的吵声。他们讲起话来,每个人都像敲一面铜磬,哐当哐当,伴随大量的傻笑。她在心里默数一、二、三,隔壁老太果然用拐杖戳了戳板壁,然后是一瘸一拐出门去的脚步声,显得比往日轻快。远一些的地方,传来苍老的咳嗽声,那沉默寡言的老头,今天也有兴致出来凑热闹了?隔壁那老太,她们语言不通,几乎没法交流。但有时她回得晚了,都会在门口给她留一盏灯,做多了菜汤往往盛一碗给她,每次站在门口,定定地看着她喝完。她想老太一定很想聊点什么,住在这荒漠里,人实在是太孤独了啊。老太隔壁是一群孤儿,他们人数众多,且茹素,每次为了多换一颗土豆一根胡萝卜,围住贩子叽叽咕咕,摇头晃脑,连说带比划,闹个不休。看他们时常撮土为香,俯仰祭拜,之后在院子里跳蹦,完全无惧辐射污染,莫非真得神灵庇佑?再过去住着一个老头,从不和任何人讲话,回回见他在窗下饮茶,院子里种着一大丛峻拔的量天尺,薄暮冥冥中,他面色阴郁。她不由得想,这老头大概靠吃仙人掌过活,像骆驼?老头家过去还有间空房,长久没再见有新的人住进来。搞不好他们这几个,就是地球上仅存的人类?总之他们几户之间,几乎不串门,也不打探彼此。都是劫后余生,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愿望,社交,绝非必要。正出神,忽听门被敲响:笃笃笃——她脸上浮现不易察觉的笑,一定是那个异域贩子!哼,偏不搭理他,谁叫他来得迟了,害她没像样的东西吃!又是一阵敲门声,笃笃笃——见屋内毫无动静,一把清越的嗓子喊道:“修炉子的,你在家吗?”他讲话带奇怪的卷舌音,听着好笑。她还是不想应门,偏偏电屏上的男人唱起了歌:“你将去往何方呀,亲爱的?哪也别去呵,哪也别去,你一直在我心底呀……”她实在不愿听这劳什子,才起身去开了门。门口是一个高鼻深目的年轻男人,披一件米白色麻布长袍,仗着肩宽腿长,倒也颇有风致的样子。见了她戴着面具的蠢相,他不由得嘴角一弯,笑容可掬地说:“嗨,好久不见!”说也奇怪,电屏上那个人工智能,就在开门这一瞬卡了壳,瞠目结舌的样子,要多蠢有多蠢。她伸手接过他递来的东西,是两枚禽蛋。这个贩子总是带来旧炉子、坏掉的空气净化器之类的让她修,留下粮食和果菜。至于其他几家,都还有些贩子需要的其他工具物件,他们便以物易物。她见贩子盯着自己双臂,笑得异样,一低头才意识到竟还没穿衣服,赶紧弹开去,三下五除二,套上一身脏不拉叽的工装,头发顺手挽个髻,洗漱,开核能炉煮咖啡。两枚禽蛋卧在手心,小小的,坠坠的,质地粗粝,颇像卵石,迎着光照一照,影影绰绰的。“搞不好,这可是地球上最后的蛋了,能孵出两只长嘴、多毛、细脚杆的鸟呢!”那贩子已拖着一堆要修的小型家电,自说自话进了屋,“如果是一公一母,大可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然后在很久很久以后,终于有一天,地球恢复了原貌,鸟飞在蓝天,鱼游在水底。你这一口下去,怕是吃掉了整个地球的未来啊,太奢侈了,不划算!”知道他惯会讲笑话拿她取乐,她用力咳一声,冷冰冰地回道:“你既然拿了来,自然是给我吃咯,难不成让我孵?现在又讲些有的没的,存心叫我吃不下怎么着?哼哼,现在整个地球,恐怕也剩不下几个人类了,自己先活下去再说!”话虽如此,她掂量再三,决定只吃一枚,留下一枚搁进冰箱。遂又在隔夜未洗的杯盏里翻寻,捡起半截香蕉。说是香蕉,其实和遭受辐射前的香蕉大相径庭,淡绿果皮上遍生细刺,小心剥开后,里面的果肉呈可疑的深紫色,口感还又涩又硬,是隔壁老太给的。她不好意思白受,拿了最后半截面包和一小盒早已过期的黄油作为交换。她咬咬牙,用力将这半截香蕉放在碗里,捣碎,蛋敲进去,又添了少许粗粮渣,几粒盐,加水搅成糊,摊在平底锅里。贩子越过她肩膀凑近来一瞧,“你就吃这个呀?”“不然呢?”她漫应着,火开大了,表皮还没凝固,底已经烧糊,一颠锅,啪嗒,掉在灶台上,慢慢滑下去。他轻轻推开她:“你先去修空气净化仪,我给你做饭。”这是贩子第一次在她的窝棚里停留。平时都是钱货两讫,童叟无欺,从不进屋的。不得不说,多一个人,窝棚里的空气都不一样了,那些杂乱的衣物、晦暗的工具架、肮脏的锅碗瓢盆,全都在黯淡中闪起光来。她捡过一只扳手,熟练地拆下盖板,回头望,贩子已放下背包,卷起袖子,洗了手,从包里取出一小袋面粉,一只橙红的小南瓜。他手法奇快,先揉面团,擀成薄片,再切碎南瓜,拌一点盐和黑胡椒末,团成一个个小包子,一道道褶子清晰可见。不一会儿空气净化仪修好,水烧开,南瓜包子蒸熟,咖啡也煮好了。贩子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骆驼奶,掺在咖啡里,又搁进一点点砂糖。掉在桌上的糖,被她扫至一处,一粒粒摁进嘴里。物质奇缺的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吃相。只是他这样的服务周到,她都不好意思不叫他一起用餐了。早饭已毕,他又收拾起碗碟,一一洗净,放在金属架上沥干。“真行啊,”她意犹未尽地吧唧嘴,“要不是地球毁了,你摆个早餐摊子,一准挣钱!”“这也算夸奖吗?”他佯装皱眉,俯身看她修那些小家电,离得那样近,几乎能感到他的体温,透过衣袍,兜头兜脑地传过来。“好啦好啦,别挡着光!”她反手一捅,把他推远,凶巴巴地骂道:“一天到晚从哪儿弄这么多破烂玩意儿!光这炉子吧,老坏老坏,都修了百八十遍,还不换,真抠门!”贩子也不申辩,只笑眯眯地垂手立在一边,把话岔开:“对了,你家水龙头,哪里来的净水?”“不知道,搬进来就是这样,”她手上不停地摆弄,头也不抬,“怎么了,你嫉妒啊?”“有点不科学,”他望向窗外,不经意似的说,“到处都给辐射尘埋了,偏偏这个洼地里,留着这么几间平房,偏偏还有干净的饮用水。你想过没有,房子是谁造的,水源会在哪里?”贩子说着,又指了指电屏,那家伙还处在死机状态:“谁在发电?卫星都毁了,又哪来的网络?”“你可真爱瞎琢磨!还嫌活着不够费事吗?”她没好声气地回他,“我倒一直想问,你那些蔬菜水果肉啊蛋啊奶啊,都是打哪儿来的?整个地球哪还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可以弄这些?莫非,你是外星人吗?”贩子微微笑着,两手一摊,“商业机密,无可奉告。”“不说?”“不能说。”“真不说?”“真不能说。”她简直气得想就着手里的锡,把他那张嘴给焊住。“其实呢,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假如某年某月某一天,你能提供等价交换物,说不定我心情大好,亲自带你去参观我的星际农场呢!又或者,我生意做大,实在忙不过来了,需要请你去打工呢?人活一世,希望总是要有的嘛——反正又不花钱!”要不是贩子一边嬉皮笑脸地补充,一边稳住她的腕子,她就差没把核能炉的孔洞全给焊死了。他还不识趣,又在那儿讲起了八卦,“欸,你说隔壁那老头和老太,怎么不干脆凑一对?就算不能给人类繁衍做贡献了,好歹实在烦闷的时候,也能找个人练练手……不,还是不行,万一他俩中的谁打输了,实在气不过,半夜爬起来放火,这一串房子不都……你也……”呸呸呸,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她索性寻了两个耳塞堵住耳朵,赶紧修完那一大堆,拾掇拾掇,掩门而去,让他没地儿聒噪去。“喂喂,你往哪个方向?”贩子把修好的物事在骆驼背上绑牢,追上来,陪着笑说,“我打算去城里转转,找水源去,同路吗?”她习惯性地退后一步,“警告你啊,我独来独往惯了,别以为我会吃人嘴软,千万千万,别跟着我!我也有商业机密,无可奉告!”说罢她摆一摆手,不回头地走了。“修炉子的,”走出去好远,那贩子还立在雪坡上,兀自挥着手,冲她背影喊:“改天见啊!”行不多时,她便独自一人在荒漠里了。除去一座座雪丘,与呼啸的风声,什么活物也没有,心里静得发虚。还说什么今天处暑,灭世之战后,地球平均温度比一个世纪前至少下降了30摄氏度,这一天一地的雪,那有半点夏天的影子?假使此刻有个人在旁边,哪怕絮叨些土味情话,也好过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吧?也不知道那个小贩走了没,本来他们还可以同路一段吧——该死的,为什么总那么嘴硬呢?她低低咒骂一声,花半个钟头爬上雪丘,又从背后解下一块金属板,蹲伏在上面,嗖一声朝雪丘另一面滑下。像这样的雪丘,还需要翻越两个,早出晚归,每天雷打不动。最后到得谷底,半架飞船就赫然眼前。那飞船一半插进雪里,凌空一半经年累月为风沙打磨,泛出暗暗银光。这铁灰色大疙瘩,边缘极薄,垂下长长短短的冰晶。整体形状不规则,线条不流畅,这里那里,乱七八糟的突起,如浑身赘生着瘤子的巨兽,庞然寂静。她打开飞船维修口那扇不起眼的小门,放下吊索,一闪身爬了进去。随着速降深入飞船腹部,光线越来越暗,她打开核能手电,一束白光掠过根根支架,条条管线,扇扇舱门,心神也越来越柔静:到家了。不知不觉,她竟哼起了歌,“你将去往何方呀,亲爱的……”当她发现自己居然在唱歌,而且是电屏男人唱的那首乱七八糟的歌,当即咬住了舌头。真奇怪,贩子进门之后,电屏男人就一直没声音了,之前明明随她怎么打都不住嘴的,难道人工智能也会有惧怕的人?一个卖瓜果蔬菜的异域贩子,又有什么可怕的?真是想破头也不明白。不过那贩子,他做的南瓜包子倒真是好吃,这会儿想起来,都还在回味那清甜啊。手电光散射回来,照亮她的脸,那张年轻、硬朗的脸上,自己都没察觉到,正漾起一圈圈,笑的涟漪。她一直下坠,下坠。文邹谨忆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插图蓝锦田(十岁)往期热文乌何有之乡南朝+僧人+乐府:以其深入佛门之心,观世间之苦乐我是白雪昭昭星星公主!领奖啦!有奖征文|谁没被凡尔赛过那么几回?人生经验值+4!芳柏司马迁:不管你信不信命,反正我信了玩过成语接龙,有没有玩过绝句接龙?教授的正确打开方式石奋:能屈不伸的官场吉祥物点击进入律簇青年人成长平台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goue.com/hgqxhj/6081.html
- 上一篇文章: 年蜂蜜价格蜂蜜批发多少钱一斤
- 下一篇文章: 樱桃价格为何起伏不定现在樱桃批发多少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