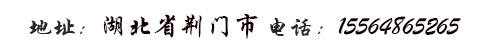大海的儿女和美人鱼
|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出生在山东沿海地区的农村,但准确的说也并不是最靠近海边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还有十几公里,但是从小就知道很多关于海的传说。那时候,人们还没有享受海滨浴场的概念,更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海洋对于我们来说是神秘的,有时候也是恐怖的,不仅是因为它的深不可测,也因为它时而慷慨、时而暴戾,时而令人毛骨悚然的面目。 曾经的海边穷的叮当响,海边的盐碱地基本长不出庄稼。姥爷说他年轻的时经常去海边买鱼,看到一家人家做饭没有柴草烧,犹豫再三,男人把院子里的一个破旧的小扫把拿去烧了。而我们“内地”的人,住在山脚下,粮草相对充足,花生收获后榨完油的花生饼可以摞起来一人多高,红薯干可以盛满一个大篓子,冬天里有这些口粮,是无比踏实的,这是海边的渔民无比羡慕的。于是,姥爷和其它壮丁经常推着一独轮车柴草、红薯去海边换鱼虾。母亲说那时从海边运来的老鼠鱼(学名绿鳍马面鲀)才八分钱一斤,现在这种鱼竟成了名贵品种,已经近百元一斤了。姥爷常说“四月八,过大鱼”,小船是不敢出海的,会被掀翻,很多人在海边看大鱼穿过,有的大鱼比屋脊都要长,老人称那些鱼是“赴龙宫赶考,浮出水面问路”的。渔民们但凡遇见了“赶考的鱼”,一定要烧纸、扔小红旗去海中,为大鱼送盘缠和引路,才能保佑自己平安。看到前几天三十多吨的鲸鱼在江苏盐城海滩搁浅的新闻,我想,我的家乡早年也许也是鲸鱼的洄游地吧。 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曾在青岛胶南县的张家楼、小口子一带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我还没有出生,他常说那里有个朋友,屁股被鲨鱼咬去了一半的朋友,还说在水里,鲨鱼闻到血的味道就会疯咬,一个男人都根本斗不过一条十几斤的鱼。母亲也在那里近距离地接触了海,在一家养殖场里种植海带。 家虽然离海不远,但第一次看到大海也是很晚的事。在我初中一年级的暑假,伯父从吉林调动回到山东,在家乡的港务局工作,我去伯父家玩,和堂哥、堂弟一起,第一次触摸到了大海和金色的沙滩。当时没有泳裤,围的礁石上有很多拿着铲子挖牡蛎的女孩子,都时一副尖酸刻薄的模样,个个皮肤黝黑,我们叫她们“海鬼子”,她们轻蔑地叫我们“庄户人”,虽然只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我们可以在码头看世界各地的船舶,这令我们感到异常新奇。还有一艘上海的船,上面全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奇怪的是他们都仅仅穿着内裤。高中一年级的暑假,我问我妈要了五块钱和同学大成去了市里,在烈日下又步行了一小时,才第一次见识了海滨浴场,当时最火爆的生意是出租游泳裤,也没有换泳衣的地方,我和大成花了一块多钱照了一张合影像就蔫不拉达地回来了,连鞋子都没脱。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师哥,他是一位爱写诗的大男孩,叫阿超,我们经常一起投稿,参加文学夏令营之类的。阿超因为家里穷,且学习成绩太差,最终脱下衣衫去了工作几乎不穿衣服的海产养殖场,再后来做了出海的渔民。一年后我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太理想,但是在那座漂亮的城市也在海边。我依然坚持写诗,有时和同学肩并肩坐在堤坝上看海,有时候独自在海滨迎风而行。任凭海浪打湿我的衣衫,间或欣喜,间或悲伤,如同痴人,走过一段人生中最纯净的季节。 九十年代初,我有两个本家哥哥,都选择了和海边的女人结婚,随后就去海边做起了渔民。渔民有许多禁忌和习俗,都是源自对大海的敬畏,筷子不可以摆放在碗上面,不说“翻”这个字眼,例如我们可以说把鱼“翻”过来吃,海边人只能说成把鱼“划”过吃。早年的渔船动力不足,通讯能力差,再加上天气预报不准精确,所以渔民要天天祭拜妈祖,如果遇到大风浪晚上不归来,村里的女人都要去海边跪着,祈求丈夫、儿子平安归来。你能想象那样的画面吗?和台湾安平的祈福平安灯一样,是一种独特的祈愿方式,只是那么悲伤。 海边更有父子、兄弟不同船的说法,就是怕万一船只出事,家里不至于没有男丁了。国外也有国王和王子从来不乘同一架飞机的惯例,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也不同机,都是为了分散风险。老家海边女人也不能上渔船,据说因为会得罪海神。实际上,在海上劳作的男人夏天通常不怎么穿衣服,有女人会分心。在海上讨饭,如果再在海神面前淫乐欢愉会得罪神明。再者实际情况是,女人和男人在船上吃喝拉撒,卫生和淡水使用等都不太方便吧,何况女人出不了力气。船上的男人都团结,渔民们相信“上了一条船,就是亲兄弟”,这不是在陆地上,可以争斗,在海里,大家的命运都在一条船上,一定是有难同当,同甘共苦的。 渔民捕鱼回来,基本上船靠岸货物卖了就啥也不管了,至于鱼类的挑拣归类、补网修船等全部交给女人或者工匠解决,渔民壮丁吃的也特别好,不能太苦了自己的肚子,尤其是听闻某某葬身海底之后,登岸后闲着就打牌、喝酒、看黄色录像带,出海更是把整箱的水果、几十斤的肉类往船上搬,这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奢侈的举动。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也在海边,那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鱼腥味和流窜的野猫,小小的城镇里有粗糙不堪的很多家酒吧和无数兼营风月事的旅店,有很多家放黄色录像的录像厅。夜晚总一些外籍船员登陆,经常会听到欧美的经典英文歌曲从破旧的店里传出来,好像《拉萨布兰卡》,外加一个霓虹灯,那就是吸引外国船员的法宝,每家店里都有几个穿着妖娆操东北口音的女孩,供外籍船员或者来谈生意的老板们玩赏。 我也经常去堂哥家去吃饭,的确因为捕鱼的生意,他们的生活比起老家已经进步了很多。我的自己的单间宿舍距离海水不过是三十米,在那里工作的两年里,听了太多关于海的传说,渔民晚上回来讲故事,说那片海里有十几米长的乌贼精,有磨台大的螃蟹王等,听了叫人毛骨悚然。有经验的老渔民常说:“陆地上有什么,海里就有什么”,地上有狗牛象,海里也有海狗、海牛、海象。不过我问过美人鱼的事情,老渔民笑着说,“想女人想疯了吧!” 九十年代的山东的台风特别多,遇到大风浪就是九死一生。堂哥跟我讲述过他经历的一次风浪,渔船在海里和一片树叶一样,被打的翻天覆地,几乎全部散架,最后想跪着船上请求妈祖都跪不稳,好在终于靠岸,算是捡了一条命,心想永远不干捕鱼的事情了,可是渔民除了捕鱼还能干什么呢?当年经常是台风过后,海边有船的村子会有几人甚至十几人葬身大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举办的葬礼时候做的都是衣冠冢,所以我们那里常说下煤矿是“埋了没死”,下海捕鱼是“死了没埋”可见是如何艰辛。那是渔民最痛苦的时候,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巨大的悲伤和绝望。 因为出海捕鱼辛苦风险大,很多渔民都不愿意自己的儿子捕鱼了,船东只好去内地找捕鱼的帮手,都是管吃管住的,当时每月有四五千的收入,也算是天文数字了,很多内地人趋之若鹜,老家有一些从安徽、河南等地来的男人,都是因为在这里做了渔民和当地女人结婚留下来的。也有人晕船干不了这种活,聪明的就开始做起了水产品、冷藏加工、干货批发销售的生意。有的女人因为丈夫去世,留下大笔产业,改嫁给了外地来的精壮小伙子,也算是两全其美。最苦的就是没了船只和男丁的渔民家庭,又没有土地,孤儿寡母的只能靠打工度日。 海上渔民作业有伏季休渔的规定,通常是暑假的两个月,后来延长到三个月,因为时鱼类产卵期,再者届时海上空气对流大,除了偷鱼的会被渔政部门捉拿之外,渔民多少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每年春节后和伏季休渔结束之后,要举行盛大的开海仪式,这是政府部分支持的“迷信”活动,也算是尊重民俗和传统吧。通常是宣读祭文,供奉丰盛的祭品食物,燃放鞭炮、叩拜等,祈求龙王和海神娘娘赐予平安丰收,人财两旺,海不扬波。早年还有唱大戏的,现在逐渐变成了一种娱乐项目。 堂哥说有一年他特别背运,因为刚开海的时候,他兴冲冲地去捕鱼,拉网的时候特别沉,以为捕到大鱼了,谁知拉出海面一看,网里的不是大鱼,却是人的尸体!咋办?赶紧收网吗?不是,拿出刀果断地把网斩断,连尸体带网永沉海底,因为在当地这是非常晦气和忌讳的事情,此后一年,堂哥衰运不断。 气好的时候,我也曾跟随老板们坐船出海,考察海里的牧场,里面挂满了海带、扇贝、海虹、梭子蟹笼子等,好像种地一样,其它同事们晕的、吐的,只有我还在开心的吃泡面和香蕉呢。老板说前几年,几个同事乘小船去海里巡逻,也偶尔撒网弄点儿鱼吃,谁知那天拉上来一只巨型海龟,年轻人要拿回去吃或者卖大价钱,好在老板说不敢妄为,把海龟放了生,还烧了香磕了头才离开那片海域。我们同事出海回来,给领导捎回来无数的海产品,扇贝有西瓜那么大的,鲍鱼和牡蛎随便吃。去年夏天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著名的海鲜一条街朋友请吃饭,一小盆煮青口(海红)花了十八欧元。在我们家乡,青口当时才五毛钱一斤,现在也不过几块钱一斤。 如今我的本家的两位兄弟们早已经发财了,十年前每人就已经拥有自己的铁壳船只,当年造价就达一百多万,可惜这几年大海里的资源几近枯竭了,加之环境污染,出海捕鱼经常不够油钱,全靠政府部门补贴过日子,好在现在可以搞一些海产品养殖,但近海的水质差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阿超师哥下海当渔民后的第五年,我几经周折去了海边的那个渔村看望他,写诗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遥远了,家里的破旧的书桌上布满尘埃,几年的努力他盖了自己的房子,也娶了媳妇,曾经文弱柔软的双手已经粗糙不堪。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好吗? 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公司里有近百位同事,就我算是沿海人,对他们来说,我是很值得羡慕的。这么多年以来,足迹已经走遍四大洋和无数的海,犹记在新西兰南岛观鲸、马耳他的假期、锡兰的海边日落、加纳利岛的海滨火山和加州海滨的灿烂阳光。去年夏天再返回家乡,到我曾工作的地方,那里已经完全废弃了如同庞贝古城,因为港口的扩建、工业的发展,行走在路上,如同在月球漫步,尘埃肆意地起舞着。远处的渔船,在渔港里瑟缩地细偎依在一起。 我们是地球的子民,海洋和土地一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看完《美人鱼》,我不禁和邓超演的刘老板一样,更觉海洋的美好和珍贵了,美人鱼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一滴干净的水,没有了一口干净的空气,就算赚再多钱,也只是死路一条”。是时候反思人类的发展模式了,如何才能让海洋健康和谐地、可持续性的发展下去,又能保持动植物多样化,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莫大的挑战和课题,我想再过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五百年,人类还是会继续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遗憾的是,人类届时还没有全部移民到外星的能力,不知道那时的地球和海洋会是什么颜色,我们看不到了,可是我们的子孙必须呼吸。 “我希望你所向往的诗意不只在远方” 鹿拾:lushi60 我终于变成了一条鱼 赞赏 人赞赏 鍋忔柟娌荤櫧鐧滈鍖椾含鍝鐧界櫆椋庡尰闄㈡瘮杈冧笓涓?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goue.com/hgfzfs/117.html
- 上一篇文章: 西澳之春上野花小袋鼠,珀斯及周边
- 下一篇文章: 胖海狮也会爬山澳洲奇遇记2